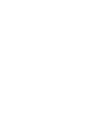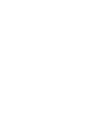南洋往事 - 第19章
蠡壳窗颇耗费功夫,辛实的休息时间其实不少,可零零散散的,凑不出个整天,因此做了小半个月才做出五扇,一齐竖起来挨着墙根排列放好,日光照上去,穿透蠡壳,有种斜阳黄昏之意,美得含蓄柔和。
这日,趁着辜镕午睡,辛实叫了詹伯来检查。詹伯瞧了以后赞不绝口,说比原先的做得还好,又夸赞辛实的手艺堪比当年老太爷请人千里迢迢从无锡接来的老匠人,那可曾是宫里出来的人。
辛实唯一自豪的就是这门傍身手艺,来到马来亚这么久,他的心一直悬着,担心大哥的生死,也忧虑自己未卜的前程,其实没真正开心过,今日被詹伯不客气地这么夸了一遭,难得地松了口气,久违地产生了些底气和信心。
脸蛋兴奋地红扑扑,他腼腆地说:“您觉得不错,我就放心了。”
詹伯笑他脸皮薄,又打量了片刻那窗,突然“咦”了声:“是不是少了东西?”
辛实看了一眼,赧然道:“您记性真好,是少了,少了字。”
损坏的那几扇窗,每扇正中间都有块脸盆大的菱格,菱格里的蠡壳上头刻了字,并填以金箔,应该是些吉祥话,可他不识字,因此所有的窗都还没刻字,想等詹伯验收完做完的这几扇,再去把原先窗上的字拓下来,印到新窗上照着刻。
从前在福州,并不觉得不识字有那么多的不便,周遭都是文盲,不差他这个。到了辜家才觉出不对劲,到处都用得上学问,遇见的个个也都是有文化的人。
辜镕不必说,有个大书房,卧室里也有一架子的书,一看就是有大文化的人。就连詹伯这样上了年纪的,也是每日会看一份报纸。
这些天待下来,他简直有些抬不起头,说自惭吧,还有些隐隐的向往。
没多久,又下起了雨,伴着雷声轰轰,天色极快地暗了下来。
辛实已经习惯马来亚说变就变的天气,赶紧踩着木屐跑去收了衣服。晾衣绳很高,他垫着脚去够,粉白洁净的脚趾被雨水溅得水光润泽。收完衣服,他回屋里拿毛巾擦干了脚,再把毛巾投水里洗干净挂好,很快回到辜镕的院子里。
下雨的午后辜镕常常睡不安稳,应当会提前醒来。
果不其然,他才在廊下望着雨幕发了片刻呆,里头辜镕便叫他的名字了。
辛实走进去,不像头回那么莽撞,一上来就去掀被子,而是先奉茶,等辜镕醒过神,说要下床,才去伺候他换衣裤和鞋。
平时辛实总要关心他几句,要不要去如厕,或者饿不饿,今日嘴巴闭得死紧,脸色也怏怏的,像是不大高兴。
辜镕低着头,边伸手整理刚换上身的黑色短褂的衣领,边随意一问:“趁我睡觉去哪野了,又跟丫头玩牌被欺负了?”
辜家有七八个杂役,都在前院做事,辛实偶尔有次遇见洗衣的女仆,搭了把手,自此认识起来。对方有次午后打牌缺了人,抓他去凑过一次角,是种本地的赌具,跟福州的马吊很像,但赌法又不大一样。因赌注十分小,詹伯对这些仆人们私下的娱乐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辜镕耳朵坏了,可却灵得很,飞快地就听说了这事,态度很是嫌弃,说那是低俗游戏,还是跟女人打,她们每个人挣钱都很不容易,输了没本事,赢了没风度,叫他下次不准再去。
那语气,讲得仿佛辛实就是个赌鬼,牌局全是由他积极组织起来的。
辛实当时就不太高兴,他也不想去啊。
第一,他不喜欢赌钱,其次,他很抠门,钱都要存起来去暹罗,不能够乱花的,即使赌注非常少,就是输上一整日都不够买条死鱼的,也不能够拿去赌。
那次稀里糊涂跟着去了完全是没反应过来,后来人家再来找他,他就学聪明了,拿辜镕当借口搪塞过去,一听说辜镕等着他伺候,那些丫头们个个脸色惨白,赶紧走啦。
辛实嚷嚷:“没去打牌,你老记着这件事,总爱提,可我就只去过一次。”
辜镕笑了一声,笑意盎然地抬起眼,单薄的双眼皮折痕柳叶似的折起,显得凌厉的面孔温和许多。他说:“谁知道你去过几次。一个未婚的男人,常常凑到女人堆里,你是喜欢里头的哪个小丫头?没出息。”
这话原本是说来臊辛实,十九了,却生得这么瘦弱,家里还穷,他先前不经意问过,知道了辛实不仅未经人事,在福州老家,连小姑娘的面也没怎么见过,更加没定过亲,或许连男女之间是个什么情愫都不明白。
可说完了,瞧见辛实又气又窘,红色的嘴唇也不高兴地向下紧抿着,自己心里却没觉出开心来,反而不自在,烦闷,疑心他是真看上了哪个丫头。
心里忍不住怪辛实目光短浅,本来就是个乡下小子,再配个乡下丫头,往后祖祖辈辈都不必出头了。
辛实原本心里就难受,听见辜镕还拿他解闷,还是那种大人逗孩子似的,不大尊重的逗法,顿时臊眉耷眼的,不说话了。
真把他欺负得不做声了,辜镕又觉得没意思,抬手轻轻地去拽辛实垂在自己肩旁的袖子,辛实被他扯得整个上半身微微地晃了晃,藏在单薄绸衣里头的细腰也跟着向前挺,像杆被风吹动的竹竿,柔柔的很秀致。
“看着我。”辜镕抬起头去端详他。
辛实不能违背他的命令,不太情愿地低下头,同他对视。
外头有日光洋洋地洒在辛实的脸上,将他黑长的睫毛投影在眼尾,勾勒出一条燕尾似的深灰色线条,线条短而深,像是用了女士眼线笔,显得一双眼睛有种灵动的色彩。
辜镕的脸色虽然依旧平静得近乎冷淡,可声音柔声细语,有种哄人的情态:“同你玩笑,真不高兴了?”
辛实不经哄,心里更委屈了,郁闷地看着他,用男孩子低哑的嗓子抱怨说:“你总笑我,我就是没出息没本事,我也不想啊。”
“没出息是我说的,可谁说你没本事了,当着我的面就污蔑我。”
辛实郁闷地说:“你们都会写字,就我不会。”
这话没头没脑,辜镕凝神一想,却恍然大悟了,原来辛实自卑。收敛起脸上的笑意,他认真地问:“你想学认字?”
辛实恹恹不乐地点头,要是有条件学习,谁愿意做文盲。
辜镕看他很乖,心情转好,突然产生了传道受业的热情。从边上的桌上拿了一碟点心递给辛实,他说:“最近有事要忙,抽不出空闲,等手头事情办完,我好好教你。”
要忙的自然是林祺贞那处被盯上的港口的事宜,无论是向上疏通还是向下改善经营,都并非一日之功。他跟林祺贞除却同袍之谊,还有合作之义,眼下说是不打仗了,可雪市仍不太平,单有钱或权都不够稳健,互相借力才是长久之道。
“真的?”辛实很自然地伸手接过那盘点心,听辜镕说要教他念书,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可他担心辜镕不是又在同他玩笑吧,犹豫地把点心又放回桌上,蹲下来两只手抓着轮椅的扶手抬头仔细去确认辜镕的神情。
昏黄的日光暖融融地罩在辜镕英俊的面孔上,这人一躲不躲,就微笑着任他看。
没有促狭的意思,挺认真的,不像骗人。
辛实这才放下心,油然高兴起来,说:“辜先生,你可不许骗我,认了字,我也能像你和詹伯一样,看书写字,往后要写信,再不用麻烦别人了。”
他一笑,秀挺的鼻背耸出了几道浅浅的笑纹,眼睛也弯没了,像只毛茸茸的土狗。
瞧他高兴成这样,辜镕不由也跟着高兴,伸手去摸了一把他同样毛茸茸的短发,很柔顺细滑,比他想得还要舒服,忍不住把五指插得更深,拇指顺带还蹭了蹭辛实光洁的额角。
辛实受不了他这个摸猫摸狗的劲儿,被摸得后脖颈发痒,忍不住地想躲,可到底咬牙忍了,没躲。辜镕往后就要给他做老师了,可自己并没有学费去给他,那么就让他摸两把,做一回猫狗算啦,反正也没少块肉。
讲定念书的事情,辛实把辜镕推到书桌边,帮他换了座位。等辜镕坐定了,他随即端起那盘点心坐在靠窗的小楠竹凳上吃起来。
辜镕做事的时候不喜欢他杵在旁边,可也不许他走太远,怕突然要吩咐找不到人,于是就叫他坐窗边去,隔得不远不近的,距离正正好。
辛实现在已经不大怕他了,并不拘束,就大大方方地坐在窗下吃点心。
碟子里有好几种糕点,核桃饼是用猪油做的,混着核桃碎和杏干,用窑炉烤过,又脆又甜,可香了;斑斓糕是用椰浆和马蹄粉揉出来的,层层叠叠的白和绿,嚼起来软糯又弹牙。
他吃得很珍惜,一只手拿饼,一只手虚虚地托着下巴,一点点碎屑都没放过,小心翼翼全吃进肚子里。
其实他也不知道辜镕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爱吃点心的。第一回辜镕突然吩咐他把桌上的甜点都拿去吃的时候,他动都不敢动,心里直打鼓,傻眼地望着辜镕,冷汗都快滴下来了,很怕是自己无意间老盯着点心看叫辜镕瞧见了,让他把点心全拿走就是故意臊他的。
可辜镕脸上的笑也不像是假的,催促他好几次,最后不耐烦了,说:“是不是要我喂你?”他才敢相信辜镕只是单纯地想分点心给他吃。
吃了好几回以后,他就习惯了。辜镕给,他就吃。不给他也不会靦着脸去要。
但也不必他张嘴问,自从辜镕发现他馋嘴这个恶习,这屋里的点心基本上都落了他的肚子,种类还十分繁杂。
辛实有时候都怀疑辜镕是不是故意买来给他吃的,他心里挺高兴的,可是他绝不敢那么想,觉得自己不要脸,也觉着辜镕没有这么闲。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