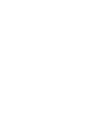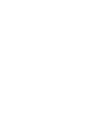南洋往事 - 第1章
一九四六年,九月,福州城。
候船厅,一个小角落,辛实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条雕花铁椅上垂着头发呆。
他是个过于年轻的男子,个子不太高大。倒并不是矮,年前借了人家的皮尺量过,有五尺三寸多。
可是瘦得厉害,像是从没吃过饱饭,两件薄薄的后肩胛骨在灰扑扑的衣裳里支棱着,嶙峋得可怜,再加上那副打不起精神的样子,整个人同周围富丽堂皇的背景格格不入。
面前不时地有人经过,但他心里掂量着一件重事,重得他没敢抬头,因此视线里只有数不清的鞋子,皮鞋、布鞋、军靴,还有女士的高跟鞋,各色的鞋笃笃作响,都匆匆的。
他什么也不关心,白生生的右手握拳搭在膝盖上,别人瞧不见,那手心底下正牢牢地攥着一个巴掌大的小布包。
布包里头放的只有一张船票,是他深夜里提着木头小矮凳到售票厅等了一整夜,大早晨售票窗口刚打开就蹿上去交钱,花了大价钱才从英国人手里买到的这么一张。
下等铺,十六人间,听说床板都只有半米宽,舱内没有厕所,要如厕了,得走到走廊尽头的公共浴室去,解个手可得费劲,全部身家得揣在身上带着去,否则回来,床铺就得被翻个底朝天。这简直是正大光明的偷窃,可如今这世道,你上哪讲理去,没办法,只能忍着,大不了少吃饭少喝水。
就是这样一张票,也是辛实花了一大半的积蓄才能买得到。
辛实是个没出过远门的孩子,福州城落地,福州城长大,长到如今十九岁,到过最远的地儿,也就是此刻脚下这块儿土,福州的南港码头。
南港的码头是前年才落成,福州是商埠,最多的就是生意人,商人里头,尤属同洋人做外贸的多,海上贸易繁盛不已,码头当然此起彼伏。
虽然没去过远地,但南港码头,辛实倒也不是头一次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家有兄弟两个,因父母早亡,他大哥十三岁起开始在外头找活路。一开始是做小工,替人擦擦皮鞋、卖卖报纸,后来,固定在一家酒楼的大后厨里头洗碗,从洗碗工到白案,从白案再到掌勺师父,他大哥花了十五年。
他被大他九岁的大哥一把屎一把尿拉扯长大,八岁起,跟了个木匠学木工,去年出了师,师父让他独立做的第一个活计,就是造这南港码头候船大厅所有值班房的门窗。
说是全部值班房,可值班房拢共也就那么几间,门窗么,加起来也就那么几十扇罢了,其他的大件,像是楼梯和天花板,还有楼上官老爷们的办公室门窗,当然是被洋人的机器厂给承包了。
也只有这种留到最后修葺的值班房,人家不乐意只为了几块扇门窗舟车劳顿再来一趟,他们这样的小木匠才能讨到几分蝇头小利。
当初第一次来的时候,候船大厅就已经初具规模,那雕花的大石膏顶,簇新的墨绿色铁质长椅,真气派!
他光顾着探头探脑地四处看,不留神差点还被地上乱堆的木楔子扎了脚底板,若不是被师父提溜着后衣领子,一定摔个大跟头。这辈子他都没看过这么好看的大楼,量尺寸的时候心里头都在畅想,这大码头还没修好就已经这么气派,等真正通航了,该多么漂亮。
今年终于通航,可他愁得脑袋都抬不起来,哪里有心情去看什么西洋景。
日头渐渐高了,辛实忍不住又抬头看了眼悬在候船大厅正中央墙壁上的那面西洋大钟,他不认识字,但钟表还略微看得懂,他的船是下午两点,此刻已经一点钟。
他是苦苦捱到此刻,看到时间将近,内心的焦躁略微得到了平息。抽空,他扫了一眼打他前边走过的人,男人都提着皮箱子,或背着包袱,女人的怀里总是抱个孩子,要么用竹篓背在身后,大家都没个高兴脸色,人人自危的气息环绕在每张麻木青白的面庞上。
这些人是去躲难。
去年夏天好不容易打跑了日本人,消息从北边传过来,大家都以为不用做亡国奴,终于可以安生过上好日子,才消停不到一年,又开始打仗。
其实能躲去哪呢,北方战火纷飞,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往南边烧。
可还是要躲,北边的往南边跑,南边的没地方跑,只好往海的另一头躲,去香港,去台湾,去南洋。
这时候,辛实感觉到后边有人靠近。他头回要出远门,正是草木皆兵,敏捷地转过头,冷不丁跟一张朴实的黑脸蛋面面相觑。
辛实吓了一跳,下意识往后仰了仰头,攥紧了手里的船票。
那人穿着一身灰扑扑的粗布对襟外衣,衣裳补了起码有七八遍,袖子上补丁叠着补丁。
瞧辛实脸上警戒的表情,那人似乎有些无措,顿了顿,在他身边的空位坐了下来,刻意压低声音朝他说:“有扒手盯上你了,就在你左边没多远。小心点,把包袱抱紧了。”
辛实心里一紧,下意识就往左边看过去。
他是个俊秀的男孩子,即使瘦得两腮都凹陷进去,也是一种面黄肌瘦的俊秀。而这张漂亮的脸蛋上,从小到大被人夸得最多的就是一双眼,不仅大,还有神,刚出生的娃娃似的,黑白分明。也正是眼睛大,眼珠一动就尤其明显,他还没瞧清左边人堆里有几个男几个女,突然有个男人站了起来,飞快转身离开了座位,匆匆没入人群。
真有扒手!
辛实悚然,瞳孔紧缩,两只细长的白手把包袱口一捏。
可惜那人走得太快,没看清长什么模样。辛实有些后怕,又有些后悔自己打草惊蛇,真不该做出那样大的反应,等一下那个扒手要是再走到他边上,他肯定认都认不出来。
呆了呆,他扭回脸,腼腆地朝黑脸蛋露出一个感谢的笑容:“兄弟,多谢你。”
黑脸蛋瞧见他笑了,松了口气,摆了摆手说:“嗨,出门在外,彼此提个醒就当积德啦。你穿得这么体面,又年轻,独个儿呆在角落里头,可不容易叫人盯上么。”
辛实低头瞧了瞧自己的衣服,黑色的对襟盘扣棉衣外衫,下头是普通的麻布长裤和布鞋。
衣服鞋袜的料子都是自己扯的布拿去找人做的,已经发旧,反复浆洗,勉强才穿了两三年,哪里称得上体面,只好在补丁少,不凑上来盯着他看一般看不出缝补过的痕迹。
人家帮了他,他也没什么好报答的,左右摸了摸兜,从包袱里头掏出个布袋子。把绑绳一松,他掏了半个玉米面饼子出来,赧然地递给黑脸蛋:“兄弟,正是饭点,来口?”
玉米面就算了,还只分半个,拿出来太寒酸,辛实其实有点不好意思,但他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再多拿点他心疼。
此去路程太远,他的目的地是暹罗,跟中国隔着一道茫茫的海,卖票的洋人操着一口难听的中国话告诉他,至少得坐上一个月的船。
这年头连衙门里做事的小官都险些吃不饱,何况他这种平头老百姓,听说船上是有餐食的,可下等舱一日只发一次,他一个半大男人,想也知道光靠一餐肯定撑不了一整天,非得自己带干粮不可。因此手里头这些干粮真是今日分出去一口,明日就得少吃一口。
黑脸蛋并不计较,爽快地就接了下来,边嚼边跟他寒暄起来:“兄弟这是上哪?”
辛实留了个心眼,并没说实情:“马来亚,我去马来亚。”
“你也下南洋?”黑脸蛋惊讶了,玉米面沫子喷出来,落到衣面上,赶紧又捡起来塞回嘴里。
抬起脸,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辛实这张白净的巴掌脸,还有大姑娘似的清秀眉眼,摇头絮絮叨叨:“就你这体格,也学那些不要命只要钱的去捞金?”
辛实心平气和地抿紧了唇,并不因黑脸蛋看扁了他而感到恼火,也不去做出解释,告诉对方自己并不是想去挣钱,只是去寻亲——又不是什么熟人,说那么多做什么。
黑脸蛋说:“兄弟,不是我多管闲事,我也认识几个去南洋谋生的伙计,个个体壮如牛,回来可也去了半条命。那地方是遍地黄金,可是把人当畜生使!进了种植园,一天最多只让你睡三个钟头,睁开眼睛就是干活,还热,比睡在热锅上还难受,你知不知道疟疾和痢疾,多少人死在这两个病上头。你可想好了,你真要去?”
辛实听得有些脸色发白,沉默片刻,微微点了点头。
这些事他心里有数,早听隔壁的小剃头匠说过。小剃头匠成天走街串巷,可有不少见识。
他当然怕呀,怕死在外头,可他非去不可。
他大哥,就是黑脸蛋嘴里下南洋捞金的人里头的一个,壮如牛,胆似豹,不怕死,就怕穷。前年,南方稍微安定下来以后,他大哥听说南洋缺工人,薪水很高,弯腰就能捡到金子,毅然决然就买了去暹罗的船票。
这些年在酒楼里没日没夜做事的积蓄,大哥带了一半走,一半则给了他,叫他别天天迷迷瞪瞪地犯傻,下雨了衣裳要记得收,一日两餐要顾好,别嘿咻嘿咻地干上活就废寝忘食。
他觉得他大哥是光看贼吃肉,没见贼挨打,南洋是好,可有去无回的更多。他是劝了又劝,抱着爹妈的牌位拦在门口不让他大哥走,就差给他大哥下跪。可他大哥,大概是实在穷怕了,怎么劝都不听,发誓说一定要出人头地了回来兄弟俩一起娶媳妇盖大屋。
大哥在船上的那一个月,他每晚每晚的睡不好,幸好他哥安安全全到了暹罗,每隔三个月都给辛实寄一封信,知道他不识字,临走前大哥特意买了坛家里过年才舍得喝的桂花酒,拜托了隔壁胡同的老童生来信了念给辛实听。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